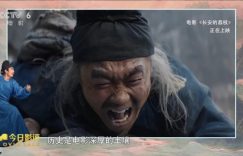《我的世界》:创造力还是“班味”?
百度云链接: https://pan.baidu.com/s/n5xxv6t7ry6aRL5xT4Y644m
# 当《我的世界》遇上好莱坞:一场注定失败的”方块变形记”
“这电影就像是用钻石镐挖泥土——费力不讨好。”北京大学博士生耿游子民在影评里这么写道。他给《我的世界大电影》打了3.5分(满分10分),这分数比苦力怕爆炸的伤害还低。作为一款卖了3亿份、火了16年的游戏改编电影,这片子到底哪儿出了问题?
电影开场就把事情搞砸了。游戏里那个让你想盖什么就盖什么、想去哪儿就去哪儿的自由世界,在银幕上变成了一连串”必须完成”的任务清单。主角们不是在创造,而是在机械地执行指令——找这个,打那个,去那里。就像耿游子民说的:”观众被迫看着角色们像被编程好的机器人一样按部就班地行动,连苦力怕爆炸都比这有意思。”
最气人的是美学选择。游戏里那些棱角分明的方块世界多酷啊,结果电影非要在”体素风格”和”真实感”之间来回横跳。一会儿把草方块做得毛茸茸的像草坪,一会儿又让角色保持着游戏里的方块手。这种不上不下的视觉效果,就像用石剑砍末影龙——完全不对路子。原版游戏那种极简主义的美感全给毁了,变成了好莱坞流水线上的又一件标准化产品。
说到角色,那些本该是背景板的NPC反而比主角团更有”人味”。主角团队?就是几个贴着标签走套路的模板:莽撞的领袖、聪明的技术宅、胆小的跟班…活脱脱从八十年代冒险片里穿越过来的。他们的冒险故事俗套得能让任何玩过现代游戏的观众翻白眼——又是找神器、打Boss、拯救世界的老三样。末影龙要是有意识,估计都得嫌这剧情太老套。
电影对游戏文化的理解还停留在二十年前。现在的《我的世界》早就不只是一个人对着屏幕搭积木了,它是全球玩家社交、创作、分享的大平台。有人用红石电路造计算机,有人复刻整个《指环王》里的中土世界,还有教育机构拿它教编程。这些鲜活的玩家文化在电影里全无踪影,仿佛主创们只看了游戏说明书就开拍了。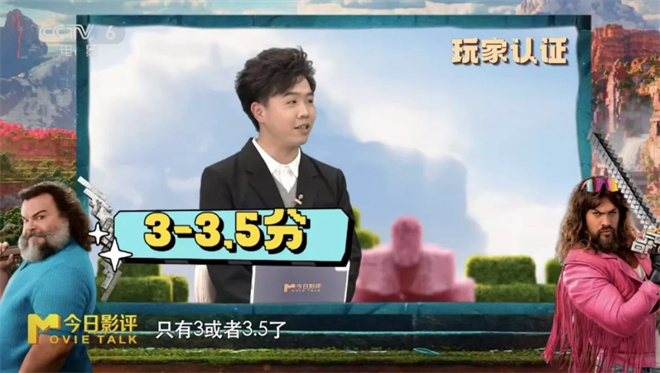
最根本的问题,是制作团队压根没搞懂《我的世界》为什么迷人。它不是关于完成任务或者打败Boss,而是关于无限可能。就像耿游子民说的:”在游戏里,砍树不是为了推进剧情,而是因为你需要木头来造你想象中的任何东西。”电影把这种自由精神压缩成了一个线性的闯关游戏,就像用命令方块强制玩家按固定路线走——完全违背了游戏的本意。
其实游戏改编电影本不必如此。《俄罗斯方块》纪录片能拍出冷战背景下的版权大战,《愤怒的小鸟》动画至少抓住了原作的卡通气质。但《我的世界大电影》偏偏选择了最偷懒的方式——套用好莱坞冒险片的模子,然后往里面硬塞游戏元素。结果就像用沙子做的砖块,看起来是那个形状,一碰就碎。
电影最后滚字幕时,我忍不住想:要是让真正玩这个游戏长大的导演来拍会怎样?也许会是主角在陌生世界醒来,没有任何任务提示,全靠自己摸索着建起第一个木头小屋;也许会是不同玩家在服务器里从互抢资源到合作建造的温暖故事;至少,不该是现在这样又一部把创意锁在箱子里的流水线产品。
说到底,《我的世界》的精髓就像它的合成系统——给你基本元素,剩下的全靠玩家自己创造。而这部电影却像直接给了张现成的合成表,还规定必须按它的顺序点鼠标。当自由创造的游戏遇上不懂创造的电影人,这场”方块变形记”从开始就注定了失败。也许下次改编时,制片方该先放下财务报表,好好进游戏里搭个房子试试——毕竟,连木斧都不会用的人,怎么可能拍得好关于创造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