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龙》之风:传承之路
百度云链接: https://pan.baidu.com/s/n5xxv6t7ry6aRL5xT4Y644m
近日,围绕向佐掌掴李小龙cos爱好者的新闻再次引发了公众的热议,这一事件不仅让人猝不及防,更勾起了对李小龙及其相关话题的复杂情感。回想起前阵子那个似乎永远无法收尾的李小龙专题,心中不禁五味杂陈,或许,是时候将那些未了的伏笔一一收拢了。
李小龙专题的制作过程颇为曲折,来来回回折腾了近二十期,却始终有个尾巴未能圆满收尾。我与李老湿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创作分歧。我热衷于玩梗与考据,喜欢将历史真实元素巧妙融入文章中,例如在《猛龙过江》篇的结尾,我曾埋下了一个大鳄项目的伏笔——《韩先生的岛》。原本计划在后续文章中揭晓谜底,即这个项目实际上就是《猛龙过江》。然而,李老湿作为编辑,考虑得更为周全。他认为许多读者是通过搜索关键词来寻找文章,我那些似是而非的玩梗会让关键词变得模糊,不利于读者的检索,因此他坚持要进行纠正。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死亡游戏》原名《冷面虎》的处理上。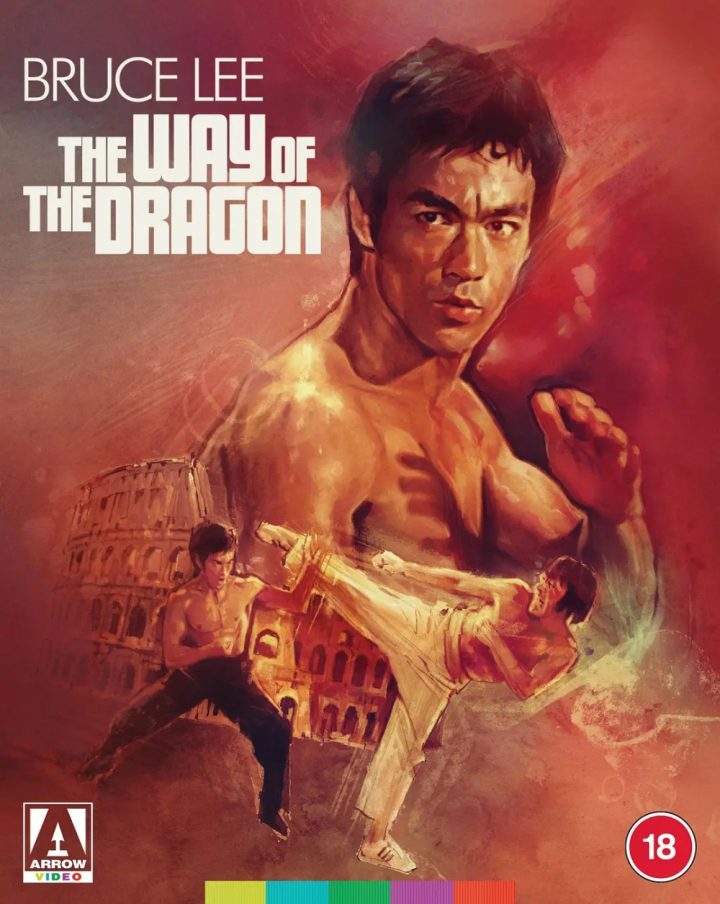
这次的向佐事件同样引发了诸多联想。众所周知,向佐是由丁佩抚养长大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李小龙有特殊情感。尽管江湖上传闻向佐小时候曾跟随李小龙的正牌弟子、菲律宾棍王伊鲁山度学过功夫,但这仅仅是传闻,我多方查证,网上的信息大多指向向佐的师父是李连杰。这个梗原本打算在甄子丹的《精武门》和李连杰的《精武英雄》相关文章中展开,但最终未能如愿。
再谈谈《死亡游戏》的地位问题。在《龙争虎斗》之后,市面上涌现了一大批被后世称为“李小龙剥削电影”的作品。许多人可能并不清楚,李小龙于1973年去世,据魏君子在电影《龙虎武师》中引用的老师傅的说法,武打片似乎一夜之间陷入了低谷,许多从业者失去了生计。然而,事实并非完全如此。当时的香港乃至整个东南亚电影市场,确实批量制作了大量“李小龙剥削电影”,试图分一杯羹。但大多粗制滥造,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让观众产生了审美疲劳,这才是武打动作片市场衰退的真正原因。
在这些剥削电影中,1973年上映的《广东小老虎》(由朱牧导演,陈元龙主演)票房惨淡,而陈元龙的师兄朱元龙(即洪金宝)的《肥龙过江》(1978年上映,与《死亡游戏》同年)却票房大卖。那时,“功夫片”这一片种尚未真正形成,还在萌芽阶段。李小龙开创了一个方向,但尚未落地生根。他最大的贡献不在于拓展这个方向,而是创造了武师这一原本在片场地位低下的角色也能独挑大梁的先例。这个先例至关重要,为后来的武术指导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刘家良就是这样一位武术指导。他与唐佳在1965年便在左派电影公司长城公司出品的《云海玉弓缘》中担任武术指导而成名,后来被邵逸夫挖走,拜入张彻门下。当时距离李小龙崭露头角还有六年多时间。刘家良和唐佳在邵氏片场风光无限,掌控着武侠片的动作演员和龙虎武师的业务,赚得盆满钵满。然而,随着张彻的特殊爱好——喜欢收弟子、捧人当导演,两人的命运发生了变化。狄龙和姜大卫因被张彻逼着当导演而产生嫌隙,刘家良虽然积极跟随张彻,但唐佳却安于现状,满足于当龙虎武师的包工头。最终,两人分道扬镳,刘家良跟着张彻去了长弓。
然而,龙虎武师出身的他能否支撑起一整部电影,仍是未知数。张彻显然也有此顾虑,虽然满口答应刘家良,却始终没有捧他做导演。李小龙的成功,证实了这个可能性的存在。张彻心高气傲,原本可能对此持怀疑态度,但当时他自身也陷入困境,远走台湾。邵逸夫作为电影圈的顶级资本家,意识到了这个可能性。1975年,两部奠定功夫片这一细分片种的电影依次上映:夏天上映的《洪拳小子》,由张彻导演,刘家良担任武术指导,傅声主演;随后,刘家良在邵氏拍摄的《神打》也面世。这两部电影真正夯实了功夫片的基础。
《洪拳小子》由张彻主导,这位邵氏老牌导演构建了功夫片应有的基本架构。比如全片以功夫为主,而非人物,开场就让主角展示整套功夫,将功夫的技能招式、杀伤特点全盘展示给观众。同时,改进了张彻传统的主角落难报仇模式,加入了一个奇形怪状的隐士高人师父,让主角从毛头小子开始成长。这种模式在1978年成龙成名的两部功夫片《蛇形刁手》和《醉拳》中得到了发扬光大。这两部作品让功夫片冲出了东南亚华人圈,打进日韩乃至全世界。而《洪拳小子》正是这种成熟模式的奠基之作。
半年后上映的《神打》,则回答了“龙虎武师没文化,到底行不行”的问题。李小龙有文化、有能力,但他的成功是机缘巧合。如果没有嘉禾的崛起和人才匮乏,没有刘亮华的投资和整个嘉禾院线的支持,李小龙可能无法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刘家良就是一个例子,邵氏家大业大,不会为一个人单独放映《唐山大兄》和《精武门》。资源没有集中,怎能成功?李小龙虽然开启了“武人话事”的时代先河,但他本人是个文化人,英年早逝,局面并未完全打开。他的《猛龙过江》因凑不齐武人班底,在武打上只重造型,缺少套招对打,变成了全片一招秒洋鬼子的局面。
张彻认为武人没文化,不能做导演,但事实并非如此。武人虽然没文化,但经验丰富,人脉广泛。谁说武术指导就不是导演呢?在《精武门》拍摄时,导演罗维只顾听收音机赌马,将镜头场景设计等工作交给李小龙的动作组完成,这种模式并不罕见。张彻拍戏时也差不多,直到后来张鑫炎找李连杰拍《少林寺》时,也没怎么干预武戏的拍摄,由专业的武人现场套招,与摄影灯光一起琢磨镜头怎么拍。因此,武术指导其实干的就是导演的活,至少是部分拍摄工作。他们可能拍不出李翰祥那种文化人的逼格,但不识字不代表没货。他们最难面对的可能是剧本,是文化人把持的最初的故事。李小龙的《猛龙过江》在故事层面就很简单,但找个好编剧就能解决。
《神打》的编剧是香港四大才子之一的倪匡,他为刘家良量身打造了这个剧本。前期工作张彻和刘家良应该一起筹划过,但两人撕破脸后,项目回到香港,在方逸华的支持下拍完了。这部电影成熟得不像“导演处女作”,尤其是镜头语言和场景调度,让人难以分辨是刘家良的处女作还是张彻亲自动手。与同样是百万大导的罗维的《新精武门》相比,《神打》在细节上堪称完美。你能相信刘家良是个新导演吗?他确实是新导演,但不代表没有积累和经验。而《神打》正是捅破这层窗户纸的作品,成为了奠定功夫片这一细分片种的佳作。而成龙的处女作《新精武门》则淹没在了那两年的“李小龙剥削电影”之中,毫无波澜。
1973年李小龙去世后,香港武打动作片市场经历了劣币驱逐良币的过程。在1978年李小龙最后的“遗作”《死亡游戏》诞生以前,功夫片这一细分片种已经在浪潮中跌跌撞撞地诞生了。关于《死亡游戏》的地位问题,李老湿认为这部电影不值一提,因为其中只有11分钟是李小龙主演的戏分,分别是对战他的两个徒弟——菲律宾棍王伊鲁山度和天勾贾巴尔的BOSS战。从电影角度来看,这个观点无可厚非。但换个角度,李小龙这个形象在我们心中已经根深蒂固,他最经典的形象之一就是《死亡游戏》中那11分钟的黄色连体裤造型。这个造型在昆汀·塔伦蒂诺的《杀死比尔》中被乌玛·瑟曼借鉴,成为全世界李小龙粉丝心中最具代表性的形象。同样,在王晶导演的《城市猎人》中,成龙与荧幕上的李小龙激情互动,用的也是《死亡游戏》里的片段。可以说,在广大影迷心中,李小龙的形象大体上只有两个:一个是传统底层人的形象,穿上汗衫踢李三脚就是《唐山大兄》,裸上身踢李三脚就是《精武门》中的陈真;另一个就是《死亡游戏》中的黄色连体裤造型。而后者似乎更加深入人心。
因此,《死亡游戏》真的那么不堪吗?未必。要深究这个问题,就要看看1973年至1978年间,那些“李小龙剥削电影”是如何塑造和剥削李小龙的。这牵涉到另一个话题:李小龙去世后,香港出现了许多“龙”字辈的武打明星,如黎小龙(何宗道)、梁小龙、唐龙、巨龙、吕小龙以及成龙,甚至还有女版李小龙茅瑛。其中,有些是纯山寨之作,但也有一些是有传承的正经作品。这些作品虽然不多,但为后来的《死亡游戏》提供了一定的拨乱反正的意味。
综上所述,李小龙的去世不仅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也为新的时代开辟了道路。虽然他的生命短暂,但他留下的影响深远,为功夫片乃至整个电影行业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而那些围绕他的电影和争议,也将继续成为影迷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